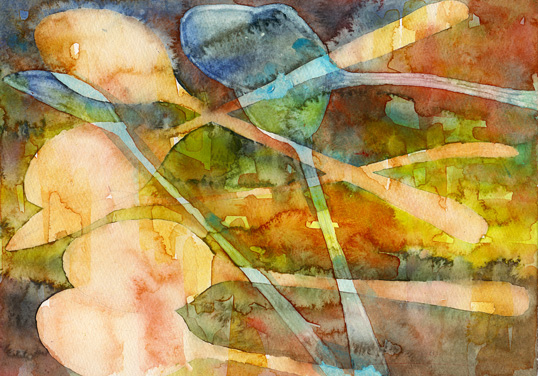女士們、先生們:
我今天來是因為拉德卡•德內馬爾科娃翻譯我的小說《呼吸鞦韆》( 英譯:《飢餓天使 The Hunger Angel》 )得了去年的「苦土文學奬」。我非常高興。我認為「苦土文學奬」設立翻譯獎是一件很棒的事。翻譯本身就是藝術。我自己不敢翻譯,雖然我的羅馬尼亞語也算流利。因為翻譯不僅僅是替換,就是說,從你的母語裡面找一個熟悉的詞語來替代另一個外語的字詞。選詞用字得要勢均力敵,這點最不容易。譯者要重新創造原文的聲音。翻譯的藝術是認真看待這些字詞,檢視它們如何觀照這個世界。翻譯必須有一種內在的迫切感,令翻譯即使有差異也儘可能貼近原文。如何找到這種四目相接的交會最為重要。這是偉大的藝術。
我學羅馬尼亞語的時候年紀已經不小了,那時我十五歲,離開農村進城裡去升中學,要到了很多年後,羅馬尼亞語才成為我的第二天性。我當時在唸大學也在機械工廠裡工作,儘管對操作完全沒有概念,卻要為那些新進口的機器翻譯操作手冊,把德文翻譯成羅馬尼亞文。我生吞活剝的硬是把它逐字翻完了,與此同時也得硬著頭皮一天到晚地說羅馬尼亞語,因為我周圍並沒有人說德語。
同樣的事物每次從某種語言轉移到另一種語言,都會脫胎換骨。這讓我醒覺到 我們自己會覺得能說母語是天經地義的,這是在不知不覺間,早就為你預留了的嫁妝。然後這一切會被另一種後天加進來又源自別處的語言來鑑定。你感覺母語是直接又沒有束縛的,就像你自己的皮膚那樣,也所以一樣的容易受傷:如果不被尊重,被鄙視,甚至被禁止使用的話。在說方言的農村長大,在中學時期學習標準德文,我在以羅馬尼亞語為官方語言的首都,很難找到自己的坐標。來到城市的頭兩年,要我在陌生的社區裡找到對的街道反而比要我在國語裡找到對的字詞來得更容易。羅馬尼亞語就像是零用錢。一旦櫥窗裡有我很想要的東西,我就會發現錢不夠用。有太多的語彙我不曉得,而我會的,要用的時候又入不敷出。然而,現在我明白在另一種語言中必須蝸行牛步,外加不確定的感覺在在都迫使我放下了小聰明,讓我會花時間欣賞事物如何在羅馬尼亞語中大變身。我何其有幸能有機會經歷這些。「燕子」在羅馬尼亞語裡面突然有了不同的面目,名字是 "rindunica",「排排坐」的意思。 這鳥兒的名字使人想到了燕子棲息在電線上,緊緊的挨成一排。之前每個夏天我都會在村子看到牠們,在我學到這個羅馬尼亞語之前。我很訝異燕子會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名字。我越來越覺得羅馬尼亞語比起我的母語來得更敏感,與我的感知更契合。不論是口語也好書寫也好,我現在可不想生活中沒有這一連串的變形。我任何一本書都沒有一句羅馬尼亞語,可是羅馬尼亞語一直都與我同在,因為我寫作的時候,它已經長成了我觀看世界的一種方式。
意象總是從語言與語言之間的縫隙冒出來。句子是觀看事物的方式,是說話者的獨特工法。每種語言看到的世界都不太一樣,各自從自身的視角發明了自己整套的語彙,用自己的方式交織成文法的網絡。每種語言的字眼都有自己不同的眼睛。
我自己不翻譯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對語言的不信任。我流亡國外的前一天,我最好的朋友來跟我訣別----我們緊緊抱在一起,心裡想著彼此再也不能相見了,因為我不會被容許再踏足羅馬尼亞,而她也不可能出國----我們都捨不得放開手。她走出大門三次,每次都走了回來。三次之後,她終於走了,頭也不回的走到大街上。我眼看著她褪色的外套越縮越小,又奇怪地,越遠越亮。我不知道是二月裡冬日的陽光,還是我的眼眶裡淚光閃閃,又也許她的外套是亮面布料做的,但是有一點我很確定:我看著她走遠,她的背影閃著光,像一隻銀湯匙。也正因為這樣,憑著直覺,我可以用文字寫出我們訣別的感覺。這是描述當下情景最好的字句。可是,銀湯匙跟外套又有什麼關係呢?完全沒有,與訣別也沒有關連。然而,作為詩的意象,湯匙與外套卻是互為彼此。
所以我對語言是存疑的。我自身的經歷告訴我,要準確,語言常常要篡奪不屬自己的東西。我不斷地問自己,為何文字的意象要像小偷一樣,為何最適切的比喻會侵佔不屬於自身的素質?要貼近真實,我們得攻其不備地將想像力逮住。唯有當某種感受掠奪另一種感受,當某種東西強搶了另一種東西的特質並且佔到便宜----唯有當現實裡不能共存的事物可以合情合理地放在同一句裡,句子才是現實的對手。
而每次我做到了,我總是快樂的。